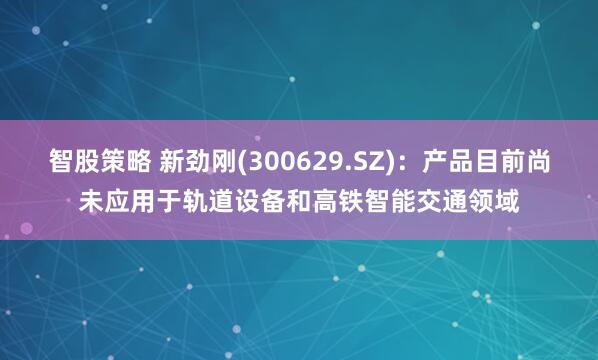本文转自:人民网-河北频道天猫配资端
朱延生 胡洪月
1980年3月初的一个傍晚,河北张家口小五台山南麓,积雪没膝深者齐腰。一个瘦小青年抱着一个麻袋,从山顶一路连出溜带滚着下山。
上山前,当地村民劝诫他,山上有深不见底的溶洞,前些年,有猎人打猎时掉了进去,尸骨至今也没找到。
回忆起过往,65岁的河北龙头山良繁场良种基地高级工程师袁德水深深叹了一口气,缓了良久接着说,“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是良种基地的希望,说什么也不能丢。”
生死小五台
20世纪70年代末,“三北”地区森林稀少且分布不均,森林覆盖率只有5.05%,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28万平方公里,每年风沙天数超过80天。
“治水之本在于治山,治山之要在于兴林。”那时,我国林业育种技术落后,良种供给率低,良种短缺成为制约“三北”防护林工程推进的重要因素之一。
“好种出好苗,好娘才有好儿孙。”当时,龙头山良繁场良种基地(以下简称“良种基地”)在全国落叶松适生区寻找优树,采集接穗(优良树种母体最顶端的穗条),然后通过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方式培育良种。
当时,一位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反馈,曾在夏天的小五台林场海拔2870米处找到了10株落叶松优树。
四月份是落叶松嫁接最佳时期。为抢夺窗口期,良种基地时任主任李文志在先派一人无功而返的前提下,又派临时工袁德水二次前往,并立下了“不管千难万险,务必把优树接穗带回来”的军令状。
“就是这片林子了,但具体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村民指着前方一片林海雪山告诉袁德水,接下来他也无能为力了。
无奈,袁德水只能自己一棵棵树辨别着……在坡度最大60多度的雪山上,他在上坡时手脚并用地爬着,不时还要停下来,掏出笔记本绘制路线图,便于日后来采接穗。
“必须趁着天黑之前,采完所有接穗后下山,否则可能就永远下不去了。”夜幕即将降临,他终于采完所有优树接穗。
“顾不上想有没有溶洞了。”袁德水抱紧装满接穗的麻袋,从山顶连出溜带滚下山……晚上八九点,他靠着意志力,拖着疲惫的身躯平安地回到小五台山下,并在一户农家住下。这时,他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
这一趟外出,袁德水用了17天,途经山西恒山、河北驼梁山、小五台和岔道等地,仅步行就100多公里,共采集了67种优质落叶松接穗。
望着疲惫不堪的袁德水和他带回来的接穗,还有桌上报销单据上仅有两张来往的车费和两张10元的住宿发票,一向刚强的李文志不禁鼻子一酸,眼中噙满了泪水。
感动之余,他亲自为袁德水写了一封表扬信。年末,袁德水这个临时工破格被场里评为“先进工作者”。“这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获奖。”这场生死考验,也成了袁德水48年林业生涯的注脚。
48年间,袁德水北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南下山西、湖北,只要有落叶松良种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行程长达26万多公里,筛选引进落叶松优良无性系428个,为基地育种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你让我干别的肯定干不好,但让我搞育种,干点实际的活,我行。”袁德水说。
灵芝“养”林种天猫配资端
小五台山的生死考验只是开始,育种之路的艰难远不止于此。
1993年,因国家政策原因,良种基地遭遇资金困难,职工们陆续离开,周边的良种基地一个个荒了。
此时,袁德水刚以临时工身份被提拔为良种基地主任不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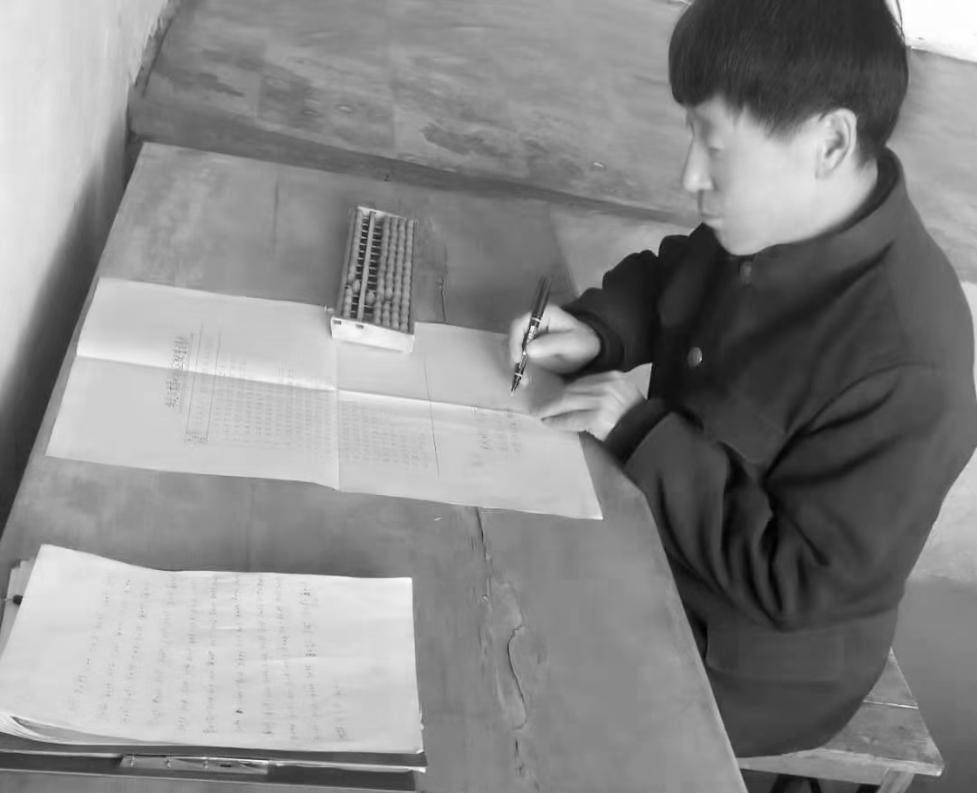
1989年,袁德水正在绘制子代林定植图。受访者供图
“咱们能不能上石家庄种苗站要点钱?”袁德水在征得龙头山林繁场原场长赵明同意后,直奔石家庄种苗站。
“你一个临时工,为什么这么执着呢?”河北省种苗站原站长钱进源反问道。袁德水不断讲述单位对良种基地的重视和良种对林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最终钱进源被袁德水的责任感与坚守打动,随即给木兰林管局领导打电话,申请了一笔资金。
有了这笔资金,良种基地暂时倒不了,但要发展,这些钱还远远不够。当时的林场领导找到袁德水,希望他可以“下山搞三产”。
“种庄稼不成误一熟,种树不当误一世。”袁德水向领导恳求道,“搞三产可以,但请允许我每周至少回一趟良种基地育种。”
“我的想法很简单,国家给了我工作,身份可以‘临时’,但育种是长期的。”袁德水总把“育种具有连续性、科学性、前瞻性,需要考虑20年以后的事”挂在嘴边。
领导同意后,袁德水便带着妻子张桂英和两名职工开始搞三产。
“要让工人跟着干,自己必须干在前。”袁德水在大棚里支起铁锅,烧开水熏蒸柞木墩、然后再用甲醛浸泡消毒,“也就5分钟,甲醛呛得鼻涕眼泪流”。
他介绍,当时灵芝种植手段落后,必须在凌晨2点无光的环境下操作,用高浓度甲醛去除污染杂质,确保种植成功。
“我也有怨气,但也得帮着他干。”张桂英想劝袁德水别太认真,但没能说服他,最终选择了默默支持。
从未出过远门的她,独自一人到辽宁采接穗;义务到良种基地做内勤;甚至她的两个儿子也被拉去修梯田……家人的支持,成了袁德水生命中的“一束光”。
2004年,国家恢复了拨款,“最艰难的岁月”过去了。

袁德水展示他记录的育种档案。人民网 朱延生摄
“我虽然是临时工,但我没拿我的工作当临时。”袁德水说。
48年间,袁德水共记录了各类基础调查数据、文字档案、配置图等档案386卷、1.52万页,总计420余万字。
正是因为他的坚持,良种基地的林业育种工作一直未断。2009年,良繁场良种基地晋升为河北省唯一一个国家重点落叶松良种基地。
由于表现出色,通过木兰林管局及省局领导的努力争取,2014年河北省人社厅特批他为国家正式工人,结束了37年的临时工生涯;后又按政策破格晋升为“高级技师”,并通过“绿色通道”方式,打破工人身份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荒山变林海
“看,这就是我当年找到的那棵优树的后代!”踏着绵软的松针,跟随袁德水进入到良种基地的二代园,他骄傲地展示着他的“孩子们”。
这些树干上都有不同的标号,像“身份证”一样记载着每株优良品种的基因密码。

袁德水和以他名字命名的优树。胡洪月摄
袁德水指着一个“43×Y205”的标号,向他的三位徒弟解释说,“43”代表母本,“205”代表父本,“Y”是袁字汉语拼音的字头,表明是自己培育出来的优良树种。
他说:“把代表我名字的字母写在树干上,是我这么多年唯一向场里提出的请求,是经过场里批准的。”
“当年发现‘205’的那片林子已经没了,但在我们的良种基地还有几十株,在‘三北’防护林,用它的种子繁育的树已有千万棵。”袁德水抚摸着树说。
48年来,袁德水和他的基地繁育的良种,为“三北”防护林、京津周围风沙源治理、国家储备林建设、再造三个塞罕坝等工程提供了3.92万斤落叶松良种,实现造林7.6万公顷。
据专家测算,以平均增益15%计算,这些树整个生长周期遗传增益可达20亿元至22亿元。
“别人说我傻,可你看这荒山,种上树就活了,人不也一样?得扎下根。”袁德水说。
“当年从雪山上滚下来时,怀里的接穗是希望。”7月21日,袁德水迎来了自己的退休仪式,他说:“退休之后我最想做的就是再去看看小五台山,虽然我现在爬不上去了。”
远处的落叶松林里,风过时整片林子都在摇晃,仿佛在诉说一个关于坚守的故事——有个年轻人曾在雪夜跋涉,有个中年人曾在绝境坚守,如今,他把故事种进土里,等着后来人收获满山林木。
【记者手记】
同一片土地,同样的风雨,林木良种总能长得更挺拔,结出更丰饶的价值。人亦如是。
原本只是一个临时工,袁德水本可敷衍度日,却把心全扑在育种上。为抢救母本从雪山滚下,护着接穗不肯松手;为筹钱维系基地,在甲醛房流着泪种灵芝……他的故事让人眼眶发热。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粒“良种”,困顿中坚守,执着浇灌,终会破土而出天猫配资端,长成生命里最挺拔的模样。
广瑞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股联社 涨价27%后,物业费收缴100%,普陀这个居民区如何做到?
- 下一篇:没有了